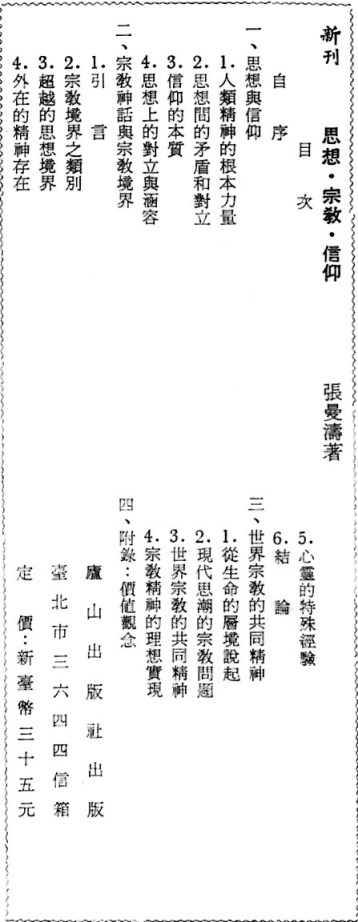一、劉薩河「因緣記」的校錄與考證
敦煌佛教文獻,在國內學術界,目前尚少人整理,本人旅法,於此侵潤多年,久有心欲盡棉力,惜終因此間之研究工作而耽擱,近得張曼濤教授之函捉,為彼所主編之佛學學報撰寫有關敦煌佛教問題,遂得此一機會,略作初步之解析工作。茲就劉薩河之因緣說起。該因緣記原由伯希和(Paul Pelliot),從敦煌莫高窟收集帶歸法國,現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東方稿本部,共三份題為「劉薩訶和尚因緣記」皆是鈔卷,本文現先予以校錄並隨予考證如次。這三份鈔卷的編號是:P、二六八○(自後省稱「甲本」),P、三五七○(自後稱稱「乙本」),P、三七二七(自後省稱「丙本」)。這三「本」原來並無點斷句讀,今除由我標附外,且對其中原用當年流行的「古」、「簡」、「通」字,諸如:囙、礼、丞等,只因減卻排印的困難,悉經我以現行的印刷字體相代換,特此說明。
(I)校錄
劉薩河因緣記(龍按:「甲本」、「乙本」、「丙本」原本並作劉薩訶和尚因緣記)
和尚俗姓劉氏。字(龍按:「甲本」誤作自,今正)薩河(龍按:「甲本」、「乙本」、「丙本」原本並作訶,據高僧傳改,下同,餘說詳後)丹州定陽人也。性好遊獵。多曾殺鹿。後忽卒亡。乃被鬼使(龍按:「甲本」作鬼所使,唯所字右旁既已見有「卜」號,故即據此符號,將此所字銷刪)擒捉。領至閻羅王所。問薩河(龍按:「甲本」河下有言字,今刪)。汝曾殺鹿已否。薩河因即詆毀(龍按:「甲本」作詆諱,「乙本」作抵諱。「丙本」作「抵毀」。抵本與詆相通,然其義為本。詆義為毀,且為扺諱。如作詆諱,則明重諱字,實係多餘;作扺諱,則只釋詆字本義之一,今皆不取,以順文意)。須臾怨家(龍按:「乙本」作怒眾)競來相證。即便招承。聞空中唱聲。薩河為鹿。
p. 34
當即身變(龍按:「甲本」作變身)成鹿。遂被箭射肚(龍按:「甲本」、「乙本」、「丙本」並作㪷,今正)下。迷悶無所覺知。即時又復人身。唯見諸(龍按:「甲本」作之,今正)地獄中。罪人無數。受諸苦毒。和尚遍歷諸地獄(龍按:「甲本」「乙本」並作諸獄,而無地字,今據「丙本」補)。忽見友(龍按:「本」作有,今正)人王叔談(龍按:「甲本」作啖,今正)。在茲受罪。乃(龍按:「甲本」作叔啖)囑和尚曰(龍按:「甲本」無曰字)。若卻至人間。請達音(龍按:「丙本」作立,今正)耗。謂我妻男(龍按:「甲本」作亦)。設齋造像。以濟幽冥。更有無數罪人。皆來相囑(龍按:「甲本」作競來囑託)又見亡過伯父。在王左右。逍遙無事。和尚問伯父。何得免其罪苦。伯父報云。我平生之(龍按:「甲本」作在)日。曾與(龍按:「丙本」作以與)家人臘(龍按:「甲本」、「乙本」並作獵,今正)月八日。共相浴佛。兼許施(龍按:「丙本」作兼施)粟六石(龍按:「甲本」作碩)承此福力,雖處三塗。且免諸(龍按:「甲本」作之,今正)苦。然吾(龍按:「甲本」作無,今正)當發心。捨粟六石(龍按:「乙本」作磧,今正)。三石已還。三石未付。倏忽之間。吾身已逝。今若施粟福盡。即受不還粟三石妄語之罪。汝可令家人。速為填納。即得生處。免歷幽(龍按:此下「甲本」誤重石至幽,共計二十一字,今刪)冥也。又見觀世音菩薩。處處救諸罪人。語薩河言。汝今卻活。可能便作沙門以否。和尚依然已為廣利群品之心。言訖(龍按:「甲本」只作訖)而墮高山。豁然醒(龍按:「甲本」作奯然醒,「丙本」作奯忽煋,今正)悟。即便出家。廣尋聖跡。但是如來諸(龍按:「甲本」、「乙本」並作如來之,「丙本」作口來之諸)行處(龍按:「甲本」、「乙本」、「丙本」並只作行,今據文意補)。菩薩行處。悉已到之。皆起塔供養。乃獲聖瑞。所到之處。無不欽仰。於是驢耳王。焚香敬禮千拜,和尚以水灑之。遂復人耳。王乃報恩。造和尚形像(龍按:「乙本」作刑像,「丙本」作刑尚)送定陽(龍按:「甲本」作楊,今正)。擎轝(龍按:「甲本」作驚譽,「乙本」、「丙本」並作驚舉)之人。若有信心之士。一二人可勝(龍按:「甲本」作勝可,然其可字之右上角既有一「V」
p. 35
號,今即據此上下字互調符號改正)。若無信心。雖百數。終(龍按:「甲本」作中,今正)不能舉。又道安【龍按:此人既非湯用彤在其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」,第二分第八章,頁一三六~一六六中,所加考究實當生於晉懷帝水嘉六年(西元三一二)與卒於晉孝武帝太元十年(西元三八五)之釋道安,亦非陳垣在其「釋氏疑年錄」,卷一,頁三,卷三,頁九五,卷四,頁一○一,頁三四五中,所予考究之長安五級寺道安、嵩山會善寺道安、趙景公寺道安與松江興聖寺道安,而實為「二教論」之作者、北周京師大中興寺、籍隸馮翊胡城、俗姓姚氏之道安,餘說詳後】法師碑記云。魏時劉薩河。仗錫西遊。至番禾。望御容谷(龍按:「甲本」、「乙本」並只作「御谷」)山遙禮。弟子怪而問(龍按:「丙本」作門,今正)曰。和尚受記。後乃(龍按:「乙本」、「丙本」並作此有)瑞像現。果如(龍按:「甲本」作而,今正)其言。和尚西至五天。曾感佛缽出現。以正始九年【龍按:正始年號有二,魏初正始有九年,東晉後燕正始只四年,此處正始九年當非指魏初之正始,則所謂九年,殆誤。今審下文言及薩河是年「遷化」,據此可知原註「正始」,當係「神[鹿/加]」之誤。唯「神[鹿/加]」亦無九年,如其原作之「九年」不誤,則似以改作太延二年(西元四三六)為妥,餘說詳後】十月廿六日,卻至秦州敷化。返西州(龍按:「乙本」、「丙本」並只作返西)。遊至(龍按:「乙本」作至遊)酒泉遷化。于今塔見在。焚身之所。有舍利(龍按:「甲本」作和,今正。「丙本」自利字起,即經接鈔於原卷之背面)。至心求者皆得。形色數般。莫(龍按:「乙本」作漠)高窟亦和尚受記。因成千龕者也。
(II)考證
就像這樣的「因緣記」我們單在所有漢文的燉煌卷冊中,所可看到者,為數恐得以百計!不過,直到如今,一些目錄學「專家」,不見則已,苟行寓目,最多也只習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標題,而有心無心地概將這樣的篇章,悉加「埋沒」,譬如:對於我現在用作校錄的這三份燉煌卷子,有些目錄的標題,無非是:
P、二六八○:「高僧傳讚」。
p. 36
|
P、三五七○:「殘佛經」。 |
P、三七二七:「背錄付法藏傳及其他禪祖史料」。 |
我得說這樣的燉煌卷冊「目錄」,很顯然地並未將其作為「目錄」的「功能」,完全發揮,即使它或經其作者加以「金」裝,這也最多只能算是略勝於無!
此刻,我敢說,這種「因緣記」的價值,如果我們正心誠意地去將它予以「善用」,倒也真是「非同小可」!單就它本身所有足可讓我們去作研究人類「文化」流變的「旁證」來講,它也等於是一個泉源。正因如此,我一向就認為燉煌的卷冊,不論其本身是否為完璧或殘餘,都是研究十一世紀中葉以前,人類文明發展的寶貴資料!不是嗎﹖此刻我們既已看完了這種「因緣記」,諒必大家都已對於劉薩河「本事」的「來龍去脈」有了相當之印象,只要大家確有興趣,改行追問「為什麼」當年的「知識份子」竟會鈔寫這樣的篇章,以及其他一連串的「為什麼」,我相信,大家一定可從此「記」之中,找出一些有關的答案!就我所知,此,「記」除可直接用以稽核劉薩河的「行誼」之外,它還很有助於我們考究中世中華哲學、文學、佛學、語言學、宗教學、歷史學、民俗學、社會學………,各種專門「學術」的演化!
茲求證明此「記」並不是什麼「無中生有」的「傑作」,我且謹將中華古籍之中,那些原經「載筆之士」,對於劉薩河的生平,特別「撰」述的長篇或短章,大致按其製作時代的先後,摘要迻錄如次:
(1)高僧傳,卷十三,興福第八,釋慧皎撰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卷,史傳部所收)。
釋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竺)慧達。姓劉。本名薩河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阿)。并州西河離石人。少好田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畋)獵。年三十。忽如暫死。經日還蘇。備見地獄苦報。見一道人云。是其前世師。為其說法。訓誨令出家。往丹陽、會稽、吳郡。覓阿育王塔像。禮拜悔過。以懺先罪。既醒。即出家學道。改名慧達。精勤福業。
p. 37
唯以禮懺為先。晉寧康中。至京師。先是簡文皇帝。於長干寺造三層塔。塔成之後。每夕放光。達上越城顧望。見此剎杪。獨有異色。便往拜敬。晨夕懇到。夜見剎下時有光。出乃告人共掘。掘入丈許。得三石碑。中央碑。覆中有一鐵函。函中又有銀函。銀函裏金函。金函裏有三舍利。又有一爪甲及一髮。髮申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神)長數尺。卷則成螺,光色炫耀。乃周敬(龍按:原註曰:王一作宣)時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。此其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即此)一也。既道俗歎異。乃於舊塔之西。更豎一剎。施安舍利。晉太元十六年。孝武更加為三層。又昔晉(龍按:原註曰:一本無此字)咸和中。丹陽尹高悝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怛。下同)於張侯橋浦裏。掘得一金像。無有光趺。而製作甚工。前有梵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胡)書云。是育王第四女所造。悝載像還。至長干巷口。牛不復行。非人力所御。乃任牛所之。徑趣長干寺。爾後年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一年)許。有臨海漁人張係世。於海口得銅花趺。浮在水上。即取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收)送縣。縣表上上(龍按:原註曰:一只作上)臺。敕使安像足下。契然相應。後有西域五僧。詣悝云。惜於天竺。得阿育王像。至鄴遭亂。藏置河邊。王路既通。尋覓失所。近得夢云。像已出江東。為高悝所得。故遠涉山海。欲一見禮拜耳。悝即引至長干。五人見像。歔欷涕泣。像即放光。照于堂內。五人云。本有圓光。今在遠處。亦尋當至。晉咸安元年。交州合浦縣。採珠人董宗之。於海底得一佛光。刺史表上。晉簡文帝敕施此像。孔穴懸同。光色一重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種)。凡四十餘年。東西祥感。光趺方具。達以剎像靈異。倍加翹勵。後東遊吳縣。禮拜石像。以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此)像於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像以,一本無此二字)西晉將末。建興元年癸酉之歲。浮在吳松江滬瀆口。漁人疑為海神。延巫祝。以迎之。於是風濤俱盛。駭懼而還。時有奉黃老者。謂是天師之神。復共往接。飄浪如初。後有奉佛居士。吳縣民朱應。聞而歎曰。將非大覺之重應乎。乃潔齋。共東雲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靈)寺帛尼及信者數人。到滬瀆口。稽首盡虔。歌唄至德。即風潮調靜。遙見二人。浮江而至。乃是石像。背有銘誌。一名惟衛。二名迦葉。即接還。
p. 38
安置通玄寺。吳中士庶。嗟其靈異。歸心者眾矣。達停止通玄寺。首尾三年。晝夜虔禮。未嘗暫廢。頃之。通適會稽。禮拜鄮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鄮縣)塔。此塔亦是阿育王所造。歲久荒蕪。示存基蹠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墌)達翹心束想。乃見神光焰發。因是修立龕砌。群鳥無敢棲集。凡近寺側。畋漁者心無作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復)獲。道俗傳感。莫不移信。後郡守孟顗。復加開拓。達東西覲禮。屢表.徵驗。精勤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誠)篤勵。終年無改。後不知所之。
(2)梁書,卷五十四,列傳第四十八,諸夷,海南諸夷,扶南國,姚思廉撰(光緒壬寅春上海文瀾書局石印乾隆年校刊二十四史所收)。查李延壽所撰之南史,卷七十八,列傳六十八,夷貊上,海南諸國,扶南國,且亦具有與梁書同樣之記敘,唯期間所用之字句,則較梁書所用者,小有差異與增減。茲為節省篇幅起見,決定只據梁書迻錄。此外,伯希和之專著「Le Fon-nan(原刊 Bulletin de I' Ecole francaise d'Extreme-Orient, Tome III(1903), pt 1, pp.258-303)」,因係主要參據梁書所有關於扶南國之記述,然並未曾提及劉薩河之「行誼」,合予說明。
扶南國。………普通元年。中大通二年。大同元年。累遣使獻方物。五年。復遣使獻生犀。又言其國有佛髮。長一丈二尺。詔遣沙門釋雲寶。隨使往迎之。先是三年八月。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。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。髮青紺色。眾僧以手伸之。隨手長短。放之。則旋屈為蠡形。案僧伽經云。佛髮青而細。猶如藕莖絲。佛三昧經云。我昔在宮沐頭。以尺量髮。長一丈二尺。放已。右旋還成蠡文。則與高祖所得。同也。阿育王即鐵輪王。王閻浮提。一天下。佛滅度後。一日一夜役鬼神。造八萬四千塔。此即其一也。吳時有尼居其地。為小精舍。孫綝尋毀除之。塔亦同泯。吳平後。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。晉中宗初渡江。更修飾之。至簡文咸安中。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。未及成而亡。弟子僧顯繼而修立。至孝武太元九年。上金相輪及承露。其後。西河離石縣。有胡人劉薩河。遇疾暴亡。
p. 39
而心下猶暖。其家未敢便殯。經十日。更蘇說云。有兩吏見。錄向西北行。不測遠近。至十八地獄。隨報重輕。受諸楚毒。見觀世音語云。汝緣未盡。若得活。可作沙門。洛下,齊城,丹陽,會稽。並有阿育王塔。可往禮拜。若壽終。則不墮地獄。語竟。如墮高巖。忽然醒寤。因此出家。名慧達。遊行禮塔。次至丹陽。未知塔處。乃登越城四望。見長干里有異氣色。因就禮拜。果是育王塔所。屢放光明。由是定知必有舍利。乃群眾。就掘之。入一丈。得三石碑。並長六尺。一碑有鐵函。函中有銀函。函中又有金函。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。髮長數尺。即遷舍利。近北對簡文所造塔。西造一層塔。十六年。又使沙門僧尚伽(龍按:孫人龍考證曰:南史作加)為三層。即高祖所開者也。初。穿土四尺。得龍窟。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。可深九尺許。方至石磉。磉下有石函。函內有鐵壺。以盛銀坩。坩內有金鏤罌。盛三舍利。如粟粒大。圓正光潔。函內又有琉璃碗。內得四舍利及髮爪。爪有四枚。並為沉香色。至其月二十七日。高祖又到寺禮拜。設無[得-彳]大會。大赦天下。是日。以金缽盛地泛水利。其最小者。隱缽不出。高祖禮數十拜。舍利乃於缽內。放光旋回。久之。乃當缽中而止。高祖問大僧正慧念。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。慧念答曰。法身常住。湛然不動。高祖曰。弟子欲請一舍利。還臺供養。至九月五日。又於寺設無[得-彳]大會。遣皇太子、王、侯、朝貴等奉迎。是日。風景明和。京師傾屬觀者。百數十萬人。所設金銀供具等物。並留寺供養。并施錢一千萬。為寺基業。至四年九月十五日。高祖又至寺。設無[得-彳]大會。豎二剎。各以金罌。次玉罌。重盛舍利及爪髮。內七寶塔中。又以石函盛寶塔。分入兩剎下。及王、侯、妃主、百姓、富室所捨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。十一年十一月二日。寺僧又請高祖於寺。發般若題。爾夕。二塔俱放光明。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。製寺大功德碑文。先是。二年。改造會稽鄮縣。開舊塔。出舍利。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。及舍人孫照。暫迎還臺。高祖禮拜竟。即送還縣。入新塔下。此縣塔。亦是劉薩何所得也。晉咸和中。丹陽尹高悝。行至張侯橋。見浦中五色光。長數尺。不知何怪。乃令人於光處。掊視之。得金像。未有光趺。悝乃下車。載像還。至長干巷。首牛不肯進。乃令馭人。
p. 40
任牛所之。牛徑牽車至寺。悝因留像付寺僧。每至中夜。常放光明。又聞空中。有金石之響。經一歲。捕魚之人張係世。於海口。忽見有銅花趺。浮出水上。係世取送縣。縣以送臺。乃施像足。宛然合會。簡文咸安元年。交州合浦人董宗之。採珠沒水。放底得佛光豔。交州押送臺。以施像。又合焉。自咸和中得像。至咸安初。歷三十餘年。光趺始具。初。高悝得像後。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。昔於天竺。得阿育王造像。來至鄴下。值胡亂。埋像於河邊。今尋覓失所。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。已出江東。為高悝所得。悝乃送此五僧至寺。見像噓欷涕泣。像便放光。照燭殿宇。又瓦官寺慧邃。欲模寫像形。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。謂邃曰。若能令像放光。回身西向。乃可相許。慧邃便懇到拜請。共夜。像即轉坐放光。回身西向。明旦。便許模之。像趺先有外國書。莫有識者。後有三藏[邱-丘+冉]求跋摩識之云。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。及大同中。出舊塔舍利。敕市寺側。數百家宅地。以廣寺域。造諸堂殿。并瑞像。周回閣等。窮於輪奐焉。其圖諸經變。並吳人張繇運手。繇丹青之工。一時冠絕。
(3)續高僧傳,卷二十五,感通上,釋道宣撰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卷,史傳部所收)
釋慧達。姓劉。名窣(龍按:原註曰:蘇骨反)和。本咸陽東北。三城定陽稽胡也。先不事佛。目不識字。為人兇頑。勇健多力。樂行獵射。為梁城突騎。守於襄陽。父母兄弟三人並存。居家大富。豪侈鄉閭。縱橫不理。後因酒會。遭疾命終。備睹地獄眾苦之相。廣有別傳。具詳聖跡。達後出家。住于文成郡。今慈州東南平原。即其生地矣。見有廟像,戎夏禮敬(龍按:原註曰:禮敬一作敬禮)處于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於)治下安民寺中。曾往吳越。備如前傳。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。流化將訖。便事西返。行及涼州、番禾郡。望御谷而遙禮之。人莫有曉者。乃問其故。達云。此崖當有像現。若靈相圓備。則世樂時康。如其有闕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關)。則世亂民苦。達行至肅州、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。其骨並碎。如葵子大。可穿之。今在城西古寺中。塑像手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于)上。寺有碑云。吾非大聖。遊化為業。文不具矣。爾後八十七年。至正光初。忽大(龍按:原註曰:
p. 41
一作天)風雨。雷震山裂。挺出石像。舉身丈八。形像端嚴。惟無有首。登即選石命工。彫鐫別頭。安訖還落。因遂任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住)之。魏道陵遲。其言驗矣。逮周元年。治涼州城東七里澗。忽有光現。徹照幽顯。觀者異之。乃像首也。便奉至山巖安之。宛然符會。儀容彫缺四十餘年。身首異所二百餘里。相好還備。太平斯在。保定元年。置為瑞像寺焉。乃有燈光流照。鍾聲飛嚮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響)。相續不斷。莫測其由。建復初年。像有頻落。大冢宰及齊王。躬往看之。乃令安處。夜落如故。乃經數十更以餘物為頭。終墜於地。後周(龍按:原註曰:本無此字)滅佛法。僅得四年。鄰國殄喪。識者察之。方知先鑒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監)。雖遭廢除。像猶特立。開皇之始。經像大弘。莊飾尊儀。更崇寺宇。大業五年。煬帝躬往。禮敬厚施。重增榮麗。因改舊額。為感通寺。故令模(龍按:原註曰:令模一作今橫)寫傳形。量不可測。約指丈八。臨度終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眾)異。致令發信。彌增日新。余以貞觀之初。歷遊關表。故謁達之本廟。圖像儼肅。日有隆敬。自石、隰、慈、丹、延、綏、威、嵐等州。並圖寫其形。所在供養。號為劉師佛焉。因之懲革胡性。奉行戒(龍按:原註曰:一一作誡)約者。殷矣。見姚通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通)安制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製)像碑。
(四)廣弘明集,卷十五,佛德篇(之一:「略列大唐育王古塔來歷並佛像經法神瑞跡」,原且亦經署為「唐終南山釋氏」撰)道宣撰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二卷,史傳部所收)。
(一)越州東三百七十里。鄮縣塔者。西晉太康二年。沙門慧達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遠)。感從地出。高一尺四寸。廣七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四)寸。露盤五層。色青似石而非。四外彫鏤。異相百千。梁武帝。造木塔籠之。八王曰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自,或作日)輿巡州里。今見神瑞、先、聲聖僧。備如別傳。
(二)潤州江寧縣故都。朱雀門東南。古越城東。廢長干寺內。昔西晉僧慧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惠。)達感光。掘之一丈。得三石匣。中有金函。盛三舍利并髮爪。其髮。引可三尺。放則螺旋。今有塼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瓦)塔三層。
p. 42
并剎佛殿。餘但榛木大蟲。登基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其)穢污者被打。號叫驚人。或有死者。
(三)沙州城內。廢大乘寺塔基。云是育王塔。
已前諸塔。並是姬周初。有大輪王。名為阿育。此一無憂。統臨此洲。萬有餘國。役健鬼神。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。此土有之。每發神瑞。廣如感應傳。
(1)吳郡松江。浮水石像二軀。昔西晉建興中。像浮松江。有居士朱應。接而出之。舉高七尺。於通玄寺。視背有銘,一名惟衛。二名迦葉。
(2)揚州長干寺。阿育王像者,東晉咸和中。丹陽尹高悝。見張侯浦有光。使人尋之。得一金像。無光趺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跌)。載順至長干巷口。牛不復行。因縱之。乃徑趣長干寺。後數年。東海人於海。獲銅跌浮水上。因造像所。果同。後四十年。南海獲銅光於海下。乃送像所。宛然符合。自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、唐七代。無不入內供養。光瑞如別。今在京師大興善寺。摸寫殷矣(龍按:原註曰:一本矣下有真身在廬山峰頂寺八字)。
(3)涼州西。番禾縣瑞石像者。元魏太延中。沙門劉薩河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訶)。行至番禾東北。望神(龍按:原註曰:一本無此字)御谷(龍按:原註曰:一本此下有山字)而禮曰。此上中。有佛像出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出者)。若相不具。國亂人苦。經八十七載。正光年初。風雨震山。像出(龍按:原註曰:像出一作挺出石像)。長三丈許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一丈八尺形相端嚴)。唯無其首。登即命造。隨安隨落。魏道陵落。隋初還復。立瑞像寺。煬帝西征。過之。改為感通寺。今圖寫。多依量矣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模)准。
已前神塔瑞像。開俗引凡。未明深者。由茲發言。既言殊相。方能攝心。披經討論。資啟神解。方知四魔常擾。六賊恒凌。覺而且怖。超方有日。不爾沈淪。還同無始。弘明之道。豈其然哉。至於經卷不灰。乃符火浣之布。書空不濕。便同天蓋之靈。聖寺屢陳。鍾聲流於遠近。神僧數現。受供通於道俗。斯途眾矣。備於感通記中。
p. 43
(龍按:此「篇」之內,實際尚有梁高祖的「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」與「牙像詔」,另外,同「篇」(之二,廣弘明集,卷十六)所收「奉阿育王寺錢啟」(署為「梁簡文帝」撰),均可參看,茲並不予迻錄,以省篇幅。)
(5)集神州三寶感通錄,卷上、中、下,釋道宣撰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卷,史傳部所收)。
(一)西晉會稽鄮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鄮縣)塔者。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。東去海四十里。在縣東南七十里。南去吳村二十五里。案前傳云。晉大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太)康二年。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(龍按:薩何一作屑荷)者。生在畋家。弋獵為業。得病死。蘇見一梵僧語何曰。汝罪重。應入地獄。吾閔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憫,或作愍)汝無識。且放。今洛下、齊城、丹陽、會稽。並有古塔。及浮江石像。悉阿育王所造。可勤求禮懺。得免此苦。既醒之後。改革前習。出家學道。更名慧達。如言南行。至會稽。海畔山澤。處處求覓。莫識基緒。達悲塞煩惋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冤)。投告無地。忽於中夜。聞土下鍾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鐘,下同)聲。即遷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遷)記其處。剡木為剎。三日間。忽有寶塔及舍利。從地踊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涌)出。靈塔相狀青色。似石而非石。高一尺四寸。方七寸。五層露盤。似西域于闐所造。面開窗子。四周天鈴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全)。中懸銅磬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硩)。每有鍾聲。疑此磬也。繞塔身上。並是諸佛、菩薩、金剛、聖僧、雜類等像。狀極微細。瞬目注睛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精)。乃有百千像現。面目手足。咸具備焉。斯可謂神功聖跡。非人智所及也。今在大木塔內。於八王日舁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輿)巡邑里。見者莫不下拜念佛。其舍利者。在木塔底。其塔左側。多有古跡。塔側諸暨縣。越舊都之地。………鄮縣古城。在句章東三百餘里。昔閩所都。其靈塔。即縣界孝義鄉也。地誌云。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。此其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之)一也。宋會稽內史孟顗修之。
p. 44
山有石坎。六可三尺。水味清淳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渟)。冬溫夏冷。輿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與)地誌云。阿育王。釋迦弟子。能役鬼神。一日夜。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。皆從地出。案晉沙門竺慧遠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達)云。東方兩塔。一在於此:一在彭城。今秣陵長干。又是其一。則有三矣。今以經驗。億家一塔。計此東夏。理多不疑。且見揚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楊)越。即有二塔。廣袤九域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城)故有之焉。會稽記云。東晉丞相王導云。初。過江時。有道人神彩不凡。言從海來相造。昔與育王。共遊鄮縣。下真舍利。起塔鎮之。育王與諸真人。捧塔飛行虛空入海。諸弟子攀引。一時俱墮。化為烏石。石猶人形。其塔。在鐵圍山也。太守褚府君云。海行者述。島上有聚烏石。作道人形。頗有衣服。褚令鑿取。將視之。石文悉如袈裟之狀。東海不遠島上。是徐偃王避暑之處。宮閣古基宛然。昔周穆西巡。登崑崙山。偃王乃有統焉。穆王聞之。馳還。日行萬里。偃王避之於此。晉孫恩作逆。寄仙妖以惑眾。築城自衛。其處猶存。梁祖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氏)普通三年。重其古跡。建木浮圖。堂殿房廊。周環備滿。號阿育王寺。四面山繞。林竹蔥翠。花卉間發。走飛(龍按:原註曰:走飛一作飛走)相娛。實閑放者之佳地。有碑頌之。著作郎顧胤祖文。寺東南三十五里。山上有佛石足跡。寺東北二里。山頭有佛左足跡。二所現于石上。莫測其先。寺北二里。有聖井………
(二)東晉金陵長干塔者。今在潤州江寧縣。故揚都朱雀門東(龍按:原註曰:一本無此字)南。古越城東。廢長寺內。昔西晉末。統江南。是稱吳國。於長干舊里。有古塔地。即育王所搆也。………五鳳中。毀除佛寺。此塔同千煙。而舍利潛地。吳平之後。諸僧頗依故處而居。起塔三層。既不得舊塔之基。事跡無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蕪)沒。莫之或識。至東晉咸安二年。簡文立塔三層。孝武上金相輪露盤。冥祥記云。簡文有意興搆。未遂而崩。即三層之塔。疑是先立。至孝武太元末。有并州西河沙門劉慧達。本名屑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薩)荷。見於僧傳。來尋古塔。莫知其地。乃登越城四望。獨見長干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于)有異氣。便往禮拜而居焉。時於昏夕。
p. 45
每有光明。迂記其處。掘之入地丈許。得三石碑。長六尺。中央一碑。鑿開方孔。內有鐵、銀、金三函相重。於金函內。有三舍利。光明映徹。及爪甲一枚。又有一髮。申可數尺。旋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放)則成螺。光彩照曜。咸以為育王之所藏也。即從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徒)就塔北。更築一塔。孝武加為三層。故寺有兩塔。西邊是育王古塔也。………梁大同中。月犯五車。老人星見。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。出舍利髮爪。天子幸寺。設大無礙法會。下詔曰。天地盈虛。………皆赦除之。今潤州江寧故地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基)。但有磚基三層。并剎佛殿。餘則榛木荒叢。非人所涉。示是古基而已。頻有大蟲。發塔基者。多自死。而草深人希。惟有惡獸。於中產育。或銜鹿而血污塔者。尋被打撲。號叫驚人。今去永安坊張侯橋七八(龍按:原註曰:七八一作南一)里。余本位京師曲池。日嚴池。寺即隋煬所造。昔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首)在晉蕃。作鎮淮海。京寺有塔。未有舍利。乃發長干寺塔下。取之入京。埋於日嚴塔下。施銘於上。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。咸言京師塔下舍利。非育王者。育王者。乃長干本寺。而不測其是非也。至武德七年。日嚴寺廢。僧徒散配。房宇官收。惟舍利塔。無人守護。守墌屬官。事須移徒。余師徒十人。配住崇義。乃發掘塔下。得舍利三枚。白色光明。大如黍米。并瓜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爪)一枚。少有黃色。并白髮數十。餘有雜寶琉璃古器等。總以大銅函盛之。檢無螺髮。又疑爪黃而小於人者。尋佛倍人爪。赤銅色。今則不爾。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寺下。依舊以大石函盛之。本銘覆上。埋于地府。余問隋初南僧。咸曰。爪髮梁武帝者。舍利則有疑焉。埋之。本銘置于其上。據事以量。則長干佛骨。頗移於帝里。然江南古塔。猶有神異。崇義所流。蓋蔑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篾)如也。故兩述之矣。但年歲綿遠。後人莫側。略編斯紀。以顯厥緣云。(龍按:原註曰:一本無此字)。
(三)沙州城內。廢大乘寺塔者。周朝古寺。見有塔基。相傳云。是育王本塔。才有災禍。多來求救。云云。
(四)晉義興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熙)元年。有林邑人。嘗有一舍利。每齋日放光。沙門慧邃。隨廣州刺史刀(龍按:
p. 46
原註曰:一作刁)逵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達,下同)在南。敬其光。相欲請之。未及發言。而舍利自分為二。逵聞心滅。又請留敬。而又分為三。逵欲模長干像。寺主固執不許。夜奏人長數丈告曰。像貴宣導。何故吝耶。明報聽摸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模)既成。逵以舍利。著像髻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髮)中。西來諸像放光者。多懷舍利故也。
卷中
(一)西晉愍帝建興元年。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。漁者萃焉(龍按:原註曰:萃焉一作華卒)遙見海中有二人現。浮遊水上。漁人疑為海神。延巫祝。備牲牢。以迎之。風濤彌盛。駭懼而返。復有奉五斗米道。黃老之徒曰。斯天師也。復共往接。風浪如初。有奉佛居士。吳縣華里朱膺。聞之歎曰:將非大覺之垂降乎。乃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迺)潔齋。共東雲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靈)寺帛尼。及信佛者數人。至瀆口。稽首延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迎)之。風波遂靜。浮江二人。險潮入浦。漸近漸明。乃知石像。將欲捧接。人力未展。聊試擎之。飄然而起。便舉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輿,或作舁)還通玄寺。看像背銘。一名惟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維)衛。二名迦葉。莫測帝代。而辭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書)跡分明。舉高七尺。施設法座。欲安二像。人雖數十。而了不可動。後重啟請。欻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翻)然得起。以事表聞朝庭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廷)士庶歸心者。十室而九。沙門釋法淵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開)。來自西域稱。經記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說)東方有二石像。及阿育王塔。有供養禮覲者。除積劫罪云。又別傳云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出)。天竺沙門一十二人。送像至郡。像乃立水上。不沒不行。以狀奏聞。下敕聽留吳郡。(龍按:原註曰:見高僧傳及旌異記等,或作見僧傳及旌異記)。今京邑咸陽長公主。聞斯瑞跡。故遣人往通玄寺圖之。在京起模。方欲顯相云。
(二)東晉成帝咸和中。丹陽尹高悝。往還帝闕。每見張侯橋浦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浦內)。有異光現。乃使吏尋之。
p. 47
獲金像一。西域古制光跌。並缺。悝下車。載像至長干巷口。牛不復行。悝止御者。任牛所往。遂徑趣長干寺。因安置之。揚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楊)都翕然觀拜。悟者甚眾。像於中宵。必放金光。歲餘。臨海縣漁人張侯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係)世。於海上見銅蓮花趺。丹光遊泛。乃馳舟接取。具送上臺。帝令試安悝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像)足。恰然符合。久之。有西域五僧。振錫詣悝云。昔遊天竺。得阿育王像。至鄴遭亂。藏于河濱。王路既通。尋覓失所。近感夢云。吾出江東。為高悝所得。在阿育王寺。故遠來相禁。欲一禮拜。悝引至寺。五僧見像。覷欷涕泣。像為之放光。照于堂內。及遶僧形。僧云。本有圓光。今在遠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何)外。亦尋當至。五僧即往供養。至咸安元年(龍按:原註曰:一本年下有以於兩字)。南海交州。合浦採珠人董宗之。每見海底。有光浮于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於)水上。尋之。得佛(龍按:原註曰:一本無此字)光。以事上聞。簡文帝敕施其像。孔穴懸同。光色無異。凡四十餘年。東西祥感。光趺方具。此像花臺。有西域書。諸來者。多不識。唯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惟)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。此古梵書也。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。時凡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瓦)官寺沙門慧邃。欲求摹寫。寺主僧尚恐損金色。語邃曰。若能令佛放光。迴身向西者。非余所及。邃至誠祈請。中宵聞有異聲。開殿見像。大放光明。轉坐面西。於是。乃許模之。傳寫數十軀。所在流布。至梁武帝。於光上加七樂天。并二菩薩。至陳永定二年。王琳屯兵江浦。將向金陵。武帝命將泝流。軍發之時,像身動搖。不能自安。因以奏聞。帝檢之有實。俄而鋒刃未交。琳眾解散。單騎奔北。遂上流大定。故動容表之。天嘉之中。東南兵起。帝於像前乞願。兇徒屏退。言訖。光照階宇。不久東陽、閩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關)、越皆平。沙門慧曉。長干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千)領袖。行化所及。事若風移。乃建重閣。故使藻畫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績)窮奇。登臨極目。至德之始。加造方趺。自晉迄陳。五代王臣。莫不歸敬。亢旱之時。請像入宮。乘以帝輦。上加油覆。僧為雨調。中途滂注。常候不失。有陳運否。亟涉訛謠。禎明二年。像面自西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轉)雖正還爾。
p. 48
以狀上聞。帝延入太極。設齋行道。其像先有七寶冠。飾以珠玉。可重三斤。上加錦帽。至曉。寶冠掛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挂)于像手。錦帽猶在頭上。帝聞。燒香祝曰。若國有不祥。還脫實冠。用示徵咎。仍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乃)以冠在首。至明。脫掛如昨。君臣失色。及隋滅陳。舉國露首面縛西遷。如所表焉。隋高聞之。敕送入京大內供養。常躬立侍。下敕曰。朕年老。不堪久立。可令右司。造坐像形相。使同其立本(龍按:原註曰:立本一作本立)像。送大興善寺。像既初達。殿大不可當陽。乃置北面。及明。乃處正陽。眾雖(龍按:原註曰:眾雖一作雖眾)異之。還移北面。至明。還南如初。眾咸愧謝輕略。今見在。圖寫殷矣。余摭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博)採眾傳記。合成此錄。有未廣者。庶知非加飾焉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焉云)。
(三)元魏涼州山開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門)。出像者。太武大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太)延元年。有離石沙門劉薩訶(龍按:原註曰:一作何下同)者。備在僧傳。歷遊江表。禮鄮縣塔。至金陵。開育王舍利。能事將訖。西行。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。番禾郡界東北。望御谷山遙禮。人莫測其然也。訶曰。此山當有像出。靈相具者。則世樂時平。如其有缺。則世亂人苦。經八十七載。至正光元年。因大風雨。雷震山巖。挺出石像。高一丈八尺。形相端嚴。唯無有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其)首。登即選石命工。安訖還落。魏道陵遲。其言驗矣。至周元年。涼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治涼)州城東七百澗。石忽出光。照燭幽顯。觀者異之。乃像首也。奉安像身。宛然符合。神儀彫缺。四十餘年。身首異處。二百餘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許)里。相好昔虧。一時還備。時有燈光流照。鍾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鐘)聲飛響。皆莫委其來也。周保定元年。立為瑞像寺。建德將廢。首又自落。武帝令齊王往驗。乃安首像項(龍按:原註曰:一作頂)。以兵守之。及明。還落如故。遂有廢法。國滅之徵接焉。備于周釋道安碑。周雖毀教。不及此像。開皇通法。依前置寺。大業五年。煬帝西征。躬往禮覲。改為感通道場。今仍在焉。依圖擬者非一。及成。長短終不得定。云云。
p. 49
(四)北涼河西王蒙遜。為母造丈六石像。在于山寺。素所敬重。以宋元嘉六年。遣世子興國。攻抱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於)罕。大敗。興國遂死。於佛(龍按:原註曰:一本無此字)佛氏。遜恚恨以事佛無靈。下令毀塔寺。斥眾道人。遜後行至楊述山。諸僧候於路側。望見發怒。立斬數人。爾時。將士入寺。禮拜此像。涕淚橫流。驚還說之。遜聞往視。至寺門。舉體戰悸。如有把持之者。因喚左右。扶翼而進。見像淚下若泉。即稽首禮謝。深自咎責。登設大會。倍更精到。招集諸僧。還復本業焉。觀遜之為。信佛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弗)深明。攻殺以取。豈佛之為非禁也。性以革改為先。任意肆惡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而)不至。初重法讖。譯大涅槃。願同生死。後因少忿。乃使刺客害之。今行役失利。又咎佛僧。殄寺誅僧。一何酷濫。晚雖再復。不補其愆(龍按:原註曰:作[保/言])云。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(龍按:原註曰:即流四凶之地)。崖高二里。佛像二百八十龕。光相亟發云。
卷下
今慈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并)州郭下。安仁寺西。劉薩何師廟者。昔西晉之末。此鄉本名文成郡。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。州東南不遠。高平原土。有人名薩何。姓劉氏。余至其廟。備盡其緣。諸傳約略。得一涯耳。初。何在俗。不異於凡。人懷殺害。全不奉法。何亦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尚)同之。因患死。蘇曰。在冥道中。見觀世音曰。汝罪重。應受苦。念汝無知。且放汝。今落下、齊城、丹陽、會稽。並有育王塔。可往禮拜。得免先罪。何得活已。改革前習。土俗無佛。承郭下有之。便具問已。方便開喻。通展仁風。稽胡專直。信用其語。每年四月八日。大會平原。各將酒餅。及以淨供。從旦至中。酣飲劇樂。即行淨供。至中便止。過午已後。共相讚(龍按:原註曰:一作賛)佛。歌詠三寶。乃至于曉。何遂出家。法名慧達。百姓仰之。敬如日月。然表異跡。生信愈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愈)隆。晝在高塔。為眾說法。夜入繭中。以自沈隱。旦從繭出。初不寧舍。故俗名為蘇何聖。蘇何者。
p. 50
稽胡名繭也。以從繭宿。故以名焉。故今彼俗。村村佛堂。無不立像。名胡師佛也。今安仁寺廟。立像極嚴。土(龍按:原註曰:一作士)俗乞願。萃者不一。每年正月。輿巡村落。去住自在。不惟人功。欲往彼村。兩人可舉。額文則開。顏色和悅。其村一歲。死衰則少。不欲去者。十人不移。額文則合。色貌憂慘。其村一歲。必有災障。故俗至今。常以為候。俗亦以為觀世音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昔)者。假形化俗。故名惠(龍按:原註曰:一作慧)達。有經一卷。俗中行之。純是胡語。讀者自解。胡黃河左右。慈、濕、嵐、石、丹、延、綏、銀八州之地。無不奉者。皆有行事。如彼說之。然今諸原。皆立土塔。上施柏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相)剎。繫以蠶繭。擬達之止也。何於本鄉。既開佛法。東造丹陽諸塔。禮畢已訖。西趣涼州番(龍按:原註曰:音槃。一本無此註,本作音栖槃)和(龍按:原註曰:一作禾)御谷。禮山出像。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礰而卒。形骨小細。狀如葵子。中皆有孔。可以繩連。故今彼俗。有災障者。就礰覓之。得之凶亡。不得吉喪。有人覓既不得。就左側觀世音像上取之。至夜便失。明旦尋之。還在像手。故土俗以此尚之。
(6)道宣律師感通錄,解彼宣撰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卷,史傳部所收)。
(一)問。今涼州西。番(龍按:原註曰:音槃)和縣。山裂像出。何代造耶。答曰。迦葉佛時。有利賓菩薩。見此山。人不信業報。以剎害為事。于時。住處有數萬家。無重佛法者。菩薩救之。為立伽藍。大梵天王。手造像身。初成以後。菩薩神力。能令此像如真佛不異。遊步說法教化。諸人雖蒙此導。猶不信受。于時。菩薩示行怖畏。手擎大石可落。欲下壓之。菩薩伴怖勸化。諸人便欻迴心。信敬於佛。所有殺具。變成蓮花。隨有街巷。花如種植。瑞自此方。攝化神力。菩薩又勸諸清信士。令造七寺。南北一百里。東西八十里。彌山亙谷。處處僧坊佛堂。經十三年。方得成就。同時出家。有二萬人。在七寺住。經三百年。彼諸人等。現業力大。昔造惡業。當世輕受。不入地獄。前所害者。在惡趣此。又發惡願。彼害我者。未及成聖。我當害之。若不加害。惡業便盡。我無以報。共吐大火。
p. 51
焚燒寺舍。及彼聚落。一時焚蕩。縱盜得活。又以大水。而漂殺之。無一孑遺。時彼山神。寺未破前。收取此像。遠在空中。寺破以後。下內石室。安置供養。年月既久。石生室滅。至劉薩何禮山。示其像者。前身元是利賓菩薩。身首別處。更有別緣。
(二)問。楊都長干塔、鄮塔。是育王者非。答云。是昔劉薩何感。令往楊州。上越域。望見長干有異氣。因標掘獲。如今傳所用。余問。若爾已有長干。便為佛剎不。答。非剎干也。是地之名。名隴為干。塔逼長隴之側。書不云乎。包括干越。干越名隴也。臨海鄮縣塔者。亦是育王造。是賢劫。初。佛中者。有迦葉佛。臂骨非人所見。羅漢將往鐵圍山。留小塔。其塔大。有善神。且現二魚。井中鰻蟍魚。護塔神也。其側有足跡石上者。云是前三佛所蹈處也不從地踊出。為開俗福也。昔周時。此土大有人住。故置此塔。
(三)問。今諸瑞像。多云育王第四女所造。其中幽遠。難得其實。答云。育王第四女。厥貌非妍。久而未出。常恨其醜。乃圖佛形。相好異佛。還如自身。成已發願。佛之相好。挺異於人。如何同我之形儀也。以此苦邀。彌經年月。後感佛現。忽異昔形。父具問之。述其所願。今非山、玉華、荊州、長沙、楊都高悝、及今崇敬。並是其像。或書光趺。人罕識者。育王令諸神鬼。所在將往。開悟佛法。令諸像面。莫匪女形。崇敬寺地。本是戰場。西晉末。五胡大起兵戈殺害。此地特多。地下人骨。今由見在。所殺無辜,殘酷枉濫。故諸神鬼。攜以鎮之。令此冤魂。得生善念。周滅佛法。神亦從之。隋祖載隆。佛還重起。云云。
本來。像上面由我迻錄的(5)、(6)兩種專書之有關文字,實際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卷史傳部所收的法苑珠林卷十三及十四,敬佛篇﹔卷三十一,潛遁篇﹔卷三十五,敬塔篇(釋道世撰)中,皆可見到(其有關字句與(5)、(6)兩書所有者,只是小有差異),茲為節省篇幅,亦定不予過錄。至於就自法苑珠林問世以後,國人對於劉薩何的「行誼」所作的記述,除卻上面已經校錄的那三份燉煌寫本「因緣記」之外,至少還有一些片斷的記述,譬如:
p. 52
太平寰宇記,卷三十五(樂史撰,嘉慶八年洪亮吉序,萬廷蘭刊)說:
雲巖縣………廢可野寺。在縣北一十五里。故老相傳。劉薩何坐禪處。稽胡呼堡為可野。四面懸絕。惟北面一面。通人焉。
同書。卷一百五十二說:
酒泉縣………劉師祠。在縣南。姓劉。字薩河。沮渠西求仙。回至此死。骨化為珠。血為丹。門人因立廟於此。令人致心者。謁之往往獲珠丹焉。
另外,就我所知,神僧傳,卷三(朱棣序於永樂十三年,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三卷,史傳部所收),亦有慧達傳。該傳所有的文字,實際只不過是續高僧傳所載有關文字的節錄,故不重錄,以省篇幅。
茲為證明這種燉煌的鈔本「因緣記」,實係有所憑據的「作品」,所以。我才不得不耐性地去將太平寰宇記以前的各種重要專門典籍之中,原有關於劉薩河的記載,悉予迻錄。但我可要特別聲明,那只是百分之百的迻錄,而不是「校錄」,換言之,我對其中原有的錯字,固未予以改正,且對它原有的「誤說」,亦未加以訂正。我不去將它們合行「校錄」,這當然是因我只希大家可藉它們的實際「形貌」,去查看其「撰製人」,特別是古往的「文士」所有的「著述」之「技巧」、用字之習慣、心理之趨向………,以及這樣的「著述」所有反映的社會發展之景況!假若沒有這樣的「貨色」,那麼,就當我們看到了前面經我校錄的「因緣記」之後,或許亦會將它視為燉煌「變」文中的「傑作」代表,但有了這樣的一些「貨色」,既可將此「因緣記」的「本源」多獲瞭解,我相信,大家的心力與時光,自可悉予轉注到其他的有關研究問題之「發明」!
我敢說,這種「因緣記」的製作年代,最早也只是在初唐,而且它的「藍本」,諒必仍是釋道宣的續高僧傳。至於其中所引的「道安法師碑記」,我則斷言:這位道安法師,他絕對不是一般所熟知,原來卒於晉孝武帝太元十年(西元三八五)的釋道安,
p. 53
而係續高僧傳,卷二十三,護法上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卷,史傳部所收)內載之釋道安。這位釋道安,實際是「俗姓姚,馮翊胡城人」,為「二教論」【參看:廣弘明集,卷八,辯惑篇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五十二卷,史傳部所收)】的作者,「卒於周世」建德三年(西元五七四)「五月十七日,普滅佛道二宗」之後。我對這位道安法師過去所作的「功德」,將來當行另為專文加以論述,茲且不予贅陳。
現在,依據這種「因緣記」,以及參驗上引的各種文獻所作之有關記載,我們應可確言:東晉元魏間,當時誠有一位名叫劉薩河的「凡夫」。不過,自他死後,只因他的「行誼」,一再經人故意加以「宣演」,甚至於有心「以訛傳訛」,結果他方由「凡夫」而成為「鬼怪」,由「鬼怪」而成為「仙佛」,以至成為「菩薩」的「化身」,既為「化身」,隨即就得由人塑造偶像,特建廟宇,以及特製壁畫(依據某些燉煌卷冊所有篇章的記述,他並是「禪宗」的第二十二位「宗師」,且在當年的某些莫高窟洞壁之上,遵照成規,猶得由當時那些壁「畫博士」去圖其「真容」(關於這種問題,我當另為專文加以解說,此刻不予縷陳),去讓當地的僧俗仕女,朝夕善行「供養」!
走筆到此,我且重將他的姓氏、字號、籍貫、生年、行跡及卒年,分別表列如次:
(1)姓氏:俗姓劉。或作竺者,則因當年出家人,習以「釋」字為姓,而「釋」氏既出天竺,故亦嘗用「竺」字以行代換。
(2)字號:字薩河。本或無「名」而僅以「字」行。且其字薩河,嘗亦作薩何、薩何、薩訶、薩和、窣和、屑荷、蘇何………等。蘇何既為稽湖繭字之音譯,故其用字,向無定準。余今採用薩河者,實從高僧傳。自彼出家之初,初號慧(此字因為與惠通,故亦嘗作惠)達(凡作遠者,大謬),蓋以古人信彼乃係菩薩之「化身」,且係「假形化俗」,因以為號焉。
(3)籍貫:參審各書所載,知其原有籍貫,殆不出於東晉元魏間之河汾地域。唯據高僧傳,則其原有之籍貫,當為目前山西省之離石縣所轄的山地。
p. 54
諸書咸謂彼屬稽胡。周書,卷四十九(令狐德棻等撰,光緒壬寅春上海文瀾書局石印乾隆四年校刊二十四史所收)曰:
『稽胡。一曰步落稽。蓋匈奴別種。劉元海五部之苗裔焉。或云山戎、赤狄之後。自離石以東,安定以西,方七八百里,居山谷間。』
據此解說,亦可知其祖居離石山地,且彼俗姓劉氏,並以胡字「繭」之對音漢字為「字」,皆可用以證明彼係東晉元魏間,深受漢化之「凡夫」!
(4)生年:諸書雖未明言,唯高僧傳謂彼
「年三十,忽如暫死,經日還蘇,備見地獄苦報………既醒,即出家學道,………晉寧康中(西元三七四)」,至吳越巡禮聖跡,據此推算,彼殆生於東晉穆帝永和元年(西元三四五)。
(5)行跡:東晉寧康中(西元三七四),親至吳越巡禮長干寺及鄮縣塔。後即西返,改禮河西諸聖跡。
(6)卒年:北魏延和三年(西元四三四),抵番禾,預言當地八十七年後,將有瑞像出現。太延元年(西元四三五),往來秦州涼州間。殆於次年(西元四三六),乃行轉遊肅州酒泉,西出沙礰,旋卒。俗壽竟達九十有二,亦屬罕見之「凡夫」也。既卒,先因時俗,由其邑人,或圖其「真容」,或建廟並塑像,以便「崇拜」祈「福」,殆至唐初,黃河左右之茲、隰、嵐、石、丹、延、綏、銀等八州暨燉煌仕女,無不「奉」信,如施相剎,則繫以「蠶繭」,權擬彼在生時之「棲止」所在!